一个人的“哈批” ——读艾吉的长卷散文《梯田上的哈批》

“哈批”是著名的红河梯田上的一个古村落,座落在哀牢山东南部的群山之中,村子不大不小,仅有120多户人家,北边与红河县城遥遥相对,是我们可以用双脚丈量的小地方。作者说,“这样的小村子,不要说进入不了国家、省、州的地图,在红河县地图上,它也是被密密麻麻的地名掩盖,像屋檐下躲雨的一只瓦雀,如果不是特意睁大眼睛,细细扫遍,很难见得到它的藏身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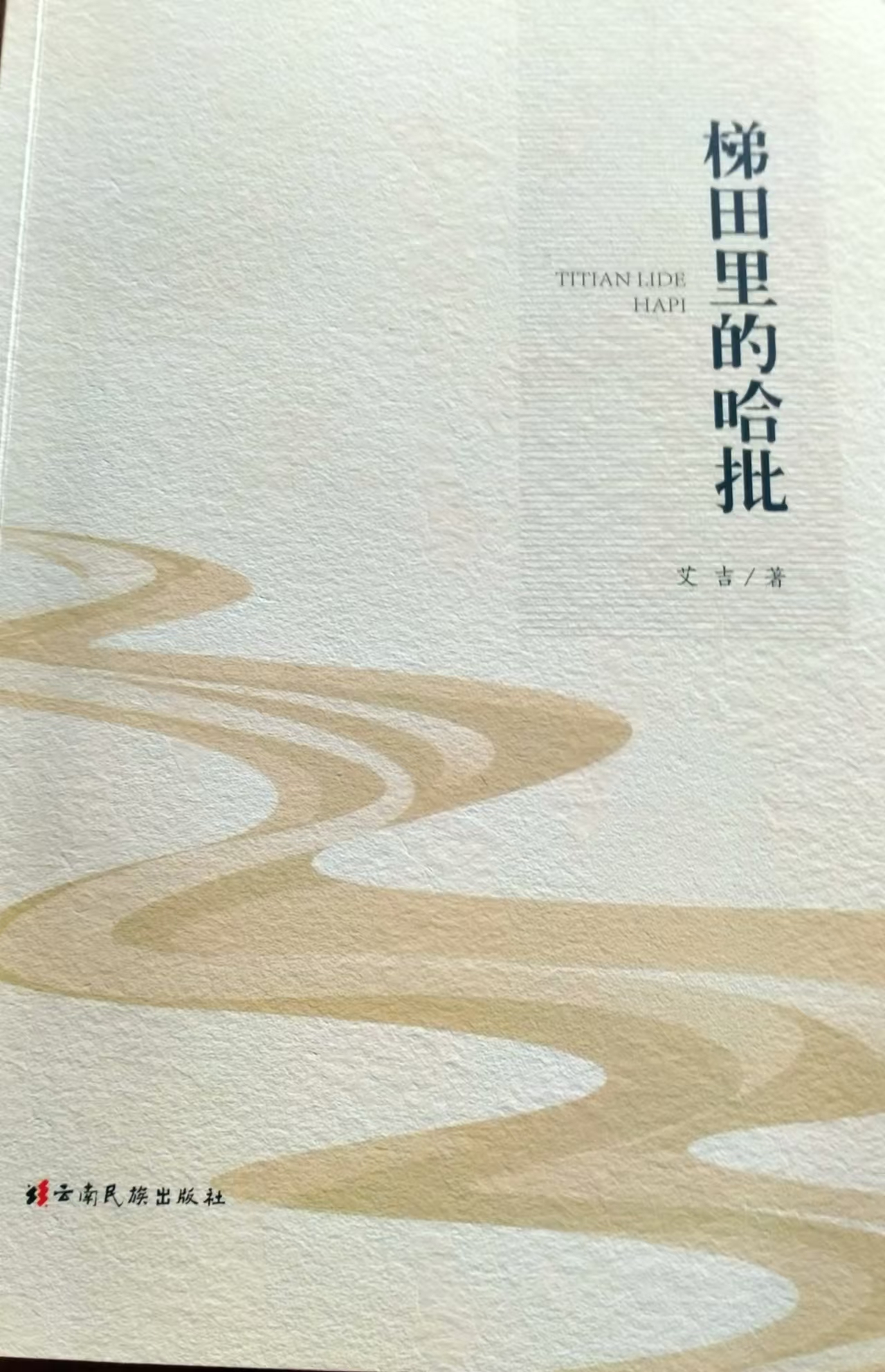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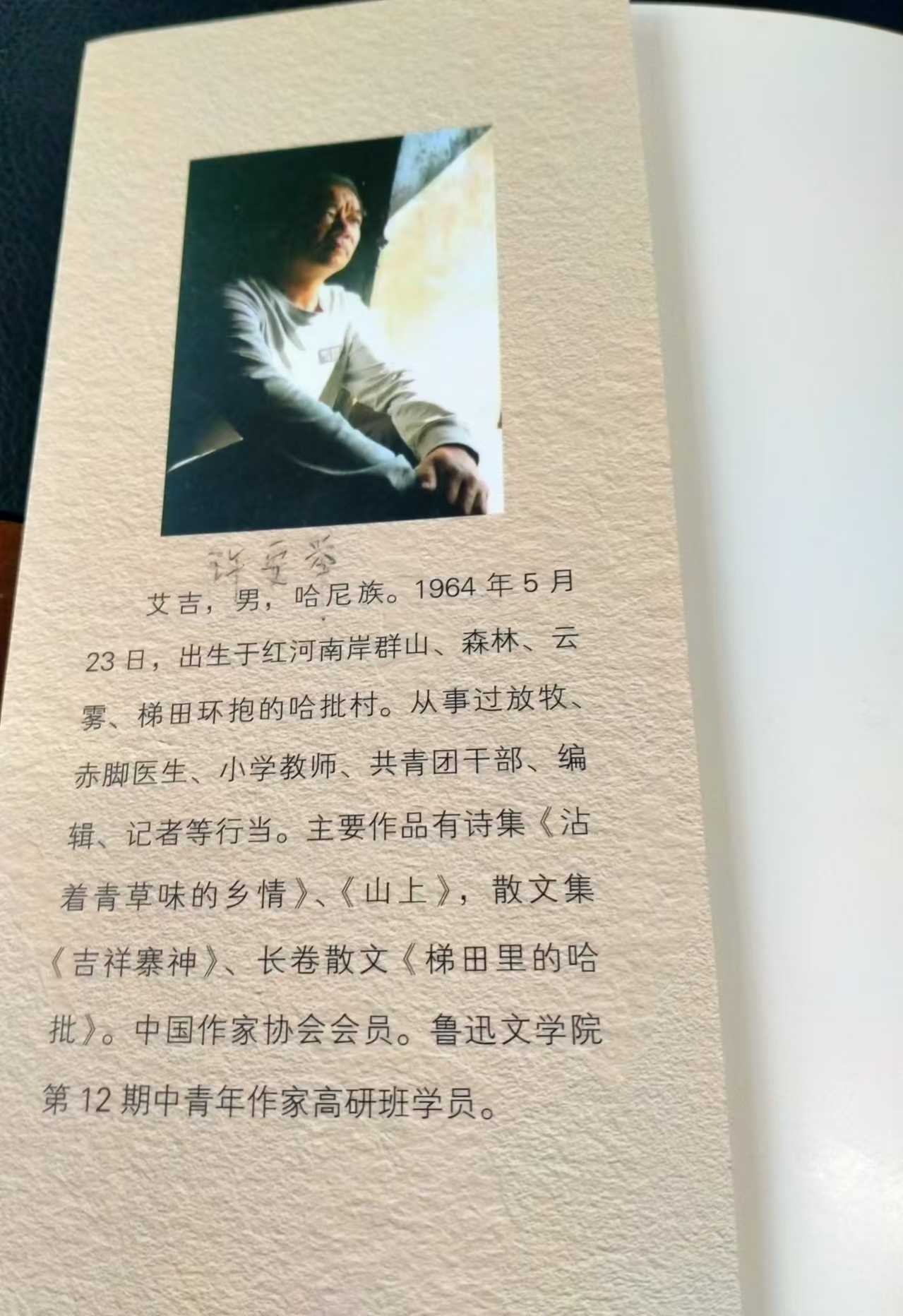
“哈批”在哈尼语中是寻衅滋事之意,因为此地旧属两个土司部落的结合部,常常发生山林纠纷,所以得此地名。关于哈批的历史,有的说,有千年,有的说,只有二三百年。作者说:历史像一团迷雾,找不到一条雾散后明朗的道路。
但就是这么一个“多事”之地,却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鸟的歌声不绝于耳。鸟如家鸡,在房顶上成群停歇,展览艳丽非凡的服饰。人会总是感到,置身于仙境般的快乐。所谓仙境,实在哪里比得上这一幅幅天然的画卷。”这是艾吉记忆中的家乡,是他的“永世家园”。艾吉说过:“这块土地不产黄金,但比产黄金的土地珍贵千倍万倍。”他从骨子里,从灵魂深处,在跟故乡日日夜夜的亲近中,对乡情、乡愁获得了更深沉的感悟。故乡对于他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他在那里出生、长大,而是使他护住了清泉般的母语,保持着诚实做人的本分。他表示,自己到死,都是不折不扣的故乡的一株庄稼。是故乡给予了他灵性,爱得痛苦,更爱得幸福。
 因此,可以说,《梯田上的哈批》是艾吉创作并献给故乡的一部具有纯粹的民间语文特质的散文文本,既是一部哈批的变迁史,也是一部个人的心灵史。作者从出生到12岁,除了几次到附近的村子做客,他“天天吃故乡的饭,喝故乡的水,熟悉每丘田、每片地,亲近每棵树、每块石头,了解每个人每件事。”他在书中竭力把他所经历和熟知的一切,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器一物,用文学的笔调呈现出来,成为一部珍贵的乡村记忆,为当代人的“乡愁”构筑了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
因此,可以说,《梯田上的哈批》是艾吉创作并献给故乡的一部具有纯粹的民间语文特质的散文文本,既是一部哈批的变迁史,也是一部个人的心灵史。作者从出生到12岁,除了几次到附近的村子做客,他“天天吃故乡的饭,喝故乡的水,熟悉每丘田、每片地,亲近每棵树、每块石头,了解每个人每件事。”他在书中竭力把他所经历和熟知的一切,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器一物,用文学的笔调呈现出来,成为一部珍贵的乡村记忆,为当代人的“乡愁”构筑了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
一翻开此书,我看到的全是细微、真实而生动的画面:层层梯田,踩着牛屎的山路出门、回家,吃山茅野菜,啃烧包谷,烤泥鳅黄鳝,在棕树竹林里唱情歌,相亲相爱……我阅读时记忆最深的是梯田中那种难以言说的大美,在作者笔下得以真切地再现。比如,作者写道“太阳照耀下,不知水里怎么会生出那么多的太阳,数也数不过来。水清,太阳是亮晶晶的,就像调皮的娃娃们,纷纷加入游戏的行列,尽情尽性,嬉笑逗闹;水浑,太阳也是明晃晃的,在丝丝污泥中满脸笑容。躲在角落的稀少的红浮萍,它们的生命力之旺盛,几天内就迅速漫延开来,一层层覆盖在水面上。一片片红浮萍,便是展览一块块精美的红毯子。人躺在上面,会是怎样的舒坦?
 作者写哈尼族同胞一生都是围着梯田转,“每一代人,条条道路都是通向梯田,前人踩凹的路,他们继续卡嚓卡嚓地踩,脚底成了戳不进刺的石板;前人爬弯的坡,他们仍旧嘿哧嘿哧地爬,脊背上烙满了牛马的蹄印。”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脚杆插进泥巴,一丘丘、一片片梯田绵亘蜿蜒在母亲宽阔的胸怀。到了降生的时辰,他们就是饱满的黄澄澄的谷穗。”两三岁时,会在火塘旁边玩灶灰,会在灶灰上面挖小田。七八岁时,父母会叫孩子去田里放鸭群。少男到了十一二岁,俨然是个劳力了。父亲会在饭桌上提起筷子语重心长地说:儿子,骨头不是用来闲着玩的,挖田是你的本命,把泥巴挖烂,就会有喂一张肚子的谷子……
作者写哈尼族同胞一生都是围着梯田转,“每一代人,条条道路都是通向梯田,前人踩凹的路,他们继续卡嚓卡嚓地踩,脚底成了戳不进刺的石板;前人爬弯的坡,他们仍旧嘿哧嘿哧地爬,脊背上烙满了牛马的蹄印。”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脚杆插进泥巴,一丘丘、一片片梯田绵亘蜿蜒在母亲宽阔的胸怀。到了降生的时辰,他们就是饱满的黄澄澄的谷穗。”两三岁时,会在火塘旁边玩灶灰,会在灶灰上面挖小田。七八岁时,父母会叫孩子去田里放鸭群。少男到了十一二岁,俨然是个劳力了。父亲会在饭桌上提起筷子语重心长地说:儿子,骨头不是用来闲着玩的,挖田是你的本命,把泥巴挖烂,就会有喂一张肚子的谷子……
这样的文字,自然、生动、细腻,像歌谣一样,音韵和谐,质朴动人,似乎可以让时光倒流,往事重现,一幅幅画面宛若雕塑般出现在我们眼前。我几个夜晚都沉迷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藏着精彩的文字、事物和故事,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这些水乳交融的文字,远远超越了一般风土人情的游记式的散文。

作者对身边那些平凡的生命,包括人、植物和动物,都倾注了不一样的热情与关切。他爱“一丘大田”,爱“梯田野味”,他写“梯田的命脉”,写“森林护卫者”,写“树群”和“树王”,他把树称之为“亲爱的树”。他写道:我想说,亲爱的树,除了这个词,我还能怎么称呼?告诉自己,那人世的纷扰,已经远去,那曾经的悲伤,不复存在。我只以树为伴,以树上的鸟声为乐。当我死去,愿意埋葬在这里,一生所求的幸福,就在这里,我将永久安宁。
他写梯田的劳动工具,如锄头、犁、镰刀、砍刀、背萝、蓑衣、谷船等等。他写道:“锄头是村民的身份证。一个村民从出生的那一刻,他的手掌就意味着要堆满一层层厚厚的老茧,起了退去,退了又起,血红血红的,他的心血就是每天通过跟锄头的接触,同大地结下终生的情缘。每个人一生中到底要挖烂多少把锄头?没人计算过。直到别人用锄头把自己埋葬在土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锄头其实是在一锄锄地挖着劳作者自己的身躯,满怀对大地的感恩之情,是万物之母的大地赐予了人们生命的能量。”那些司空见惯的劳动工具,在艾吉的笔下,变得鲜活起来,仿佛一张张黑白老照片,被他精心修复,从而变得清晰而富有色彩和质感了。

在艾吉的文字里,哈批每个个体生命从村子的各个角落走出来,走进他的世界,走进他的文字,成为故乡的主角。在《爱情像天空的云朵》《白衣裳》《乐器声声传情》《阿巴尼》等篇章中,作者甚至用小说的白描手法叙述故乡的风物和人事。这应该是一种跨文体写作,包含着作者在散文文体上的创新和探索。
艾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记录者,他也是哈批之子,他独特的经历让他能更清晰地感知故乡在新时代的常与变,在作者对往事的回忆与回乡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中,我们从《三代人的北京缘》《电灯亮了公路通了》《涌向外面世界》等篇目中感知新时代乡村的发展变化。当下,什么都在变,变“快”,变“新”,变“大”。哈批的村民也随之往前冲,走出家乡,从“小地方”奔赴“大地方”;从“小城市”奔向“大城市”。作者为此忧心忡忡,他写道:“梯田是辉煌的,与此同时,它又有极为脆弱的一面。在全球以经济为中心的一体化背景下,多少年轻人离开梯田出去外面打工,梯田放荒的严峻现实触目惊心。祖祖辈辈靠梯田赖以为生的许多村落,甚至连一丘梯田都见不到了。父母在城里打工时间长了,他们的后代,有的已经不知道梯田是什么样子。我不是预言家,说不出梯田将来的命运。我只能说,梯田和它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依然以强大的力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故乡。”
 在书中,艾吉裹挟着他的所有回忆、联想、感悟,但他并不像某些作家文本一样的抑制不住,喷涌而出,而是自由地表达,无拘无束,娓娓道来,尽情吟唱。他有时好像是自言自语,有时又像是在向亲人倾诉,似乎不在乎语言和叙述的技巧,而进入了自由自在的境界。事实上,在网络时代,话语的秩序正在重组,如何表达新的经验,每个作家都在寻找新的语言和新的叙述方式。而艾吉却固守民间立场,他在很多篇章都使用了非常本真的哈尼族诗性土语,表达出普通话所不能描述的事物,也描摹出了作者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他说:“一个刚从田里拔出脚,全身沾满泥巴的乡亲,有本事看见什么便会脱口而出几句生动得让人捧腹弯腰的话。我一辈子绞尽脑汁,想不出那样精彩的语言。而这样的语言,在他们的生活中却是每时每刻都在创造,都在使用,谁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哪怕骂人的粗话,是那样的富有艺术感,耐人寻味。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书本。”所以,在我看来,作者在不经意间,就写出了一部具有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意义的文学文本,这样的文本耐人寻味,历久弥新,其价值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在书中,艾吉裹挟着他的所有回忆、联想、感悟,但他并不像某些作家文本一样的抑制不住,喷涌而出,而是自由地表达,无拘无束,娓娓道来,尽情吟唱。他有时好像是自言自语,有时又像是在向亲人倾诉,似乎不在乎语言和叙述的技巧,而进入了自由自在的境界。事实上,在网络时代,话语的秩序正在重组,如何表达新的经验,每个作家都在寻找新的语言和新的叙述方式。而艾吉却固守民间立场,他在很多篇章都使用了非常本真的哈尼族诗性土语,表达出普通话所不能描述的事物,也描摹出了作者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他说:“一个刚从田里拔出脚,全身沾满泥巴的乡亲,有本事看见什么便会脱口而出几句生动得让人捧腹弯腰的话。我一辈子绞尽脑汁,想不出那样精彩的语言。而这样的语言,在他们的生活中却是每时每刻都在创造,都在使用,谁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哪怕骂人的粗话,是那样的富有艺术感,耐人寻味。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书本。”所以,在我看来,作者在不经意间,就写出了一部具有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意义的文学文本,这样的文本耐人寻味,历久弥新,其价值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作者简介:
杨杨,本名杨家荣,云南省通海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玉溪市文联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混沌的夏天》《摇晃的灵魂》《雕天下》《通海大地震真相》《大学之光》等文学专著。曾获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国家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奖、冰心散文奖。
责任编辑:李聪华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53120240002 网络视听许可证2510473号 滇ICP备11001687号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电话、涉未成年人专用举报电话:0873-3055023 涉未成年人专用举报邮箱:hhwjjbb@163.com
中共红河州委宣传部主管 红河网版权所有 未经红河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