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蕴藉丰沛的哈尼农耕文明简史
——读艾吉长卷散文《梯田里的哈批》

在看到艾吉《梯田里的哈批》(云南民族出版社2022年12月第1版)这部散文集之前,该书的责编、诗人聂勒告诉我,这是他编过的最好的散文作品。他盛赞此书语言鲜活,文字灵动。聂勒是颇挑剔的资深编辑,这位自信的诗人向来吝于赞美他人的文笔。
读了艾吉的书后,我欣然赞同聂勒给予它的好评。然而,仅清词丽句散落如星辰、语言丰饶激荡人心之类的文学审美评价,我感觉还不够全面;关于这部别具情怀的乡土著作,其蕴藏良多的人文社科价值尤其不容低估。
坦率说吧,我阅读《梯田里的哈批》时,内心不时会涌起清澈的激情。想起遥远的乡间童年生活,想到在现代化进程中沉沦的故乡,忍看良田沃野被高楼湮没,我真希望此书是出自我手——书写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美丽村庄,赞美勤劳智慧的民族,为父老兄弟立传,描绘生机勃勃的田园,用诗意丰沛的锦绣文字留住辉煌的乡土文明画卷,顺便深情地高唱一曲传统农耕文明的挽歌。
感谢诗人艾吉,这个从骨子和灵魂深处热爱着乡土文化,格外熟悉农村社会生态,深刻懂得农民日常生活苦乐,特别能体会草木野鸟之心的写作者,他以拳拳赤子之心,以诚挚纪实且抒情气息浓郁的笔法,以真诚欣赏而近于夸张的喜剧笔调,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讲”的生动语言,为我们倾情奉献了一部真正关切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属于寻常百姓审美,值得认真研读和收藏的“乡土社会入门书”、“哈尼乡村生活指南”:它既是蕴藉丰沛、引人入胜的哈尼乡村私人志,也是趣味盎然、通俗易懂的农耕文明简史。
换个说法,《梯田里的哈批》是一部适合普罗大众阅读的好书:远离故园、漂泊都市的游子,读之可大慰孤怀,缓解乡愁;从未接触过“三农”的城里人,读之可了解传统的乡土社会、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该书甚至可作当代中小学生课外必读书目——孩子们读了,会了解露珠闪烁的农耕文化,热爱烟火灿烂而芬芳的乡土文明,热爱溪水奔流、草木葳蕤、庄稼繁茂、鸟唱蛙鸣的自然界。
艾吉倾心书写的哈批,是他的故乡——一个地处红河南岸群山之中,隐藏于李和山腹部,仅有120多户人家的哈尼小山村。在哈尼族聚居的红河南岸山地,哈批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地,即使在红河县地图上,也只“像屋檐下躲雨的一只瓦雀,如果不是特意睁大眼睛,细细扫遍,很难见得到它的藏身之处”。
据《红河县地名志》所说,哈批系哈尼语的音译,即“寻衅”之意。因其旧属溪处、瓦渣两个土司区域结合部,山林纠纷不断,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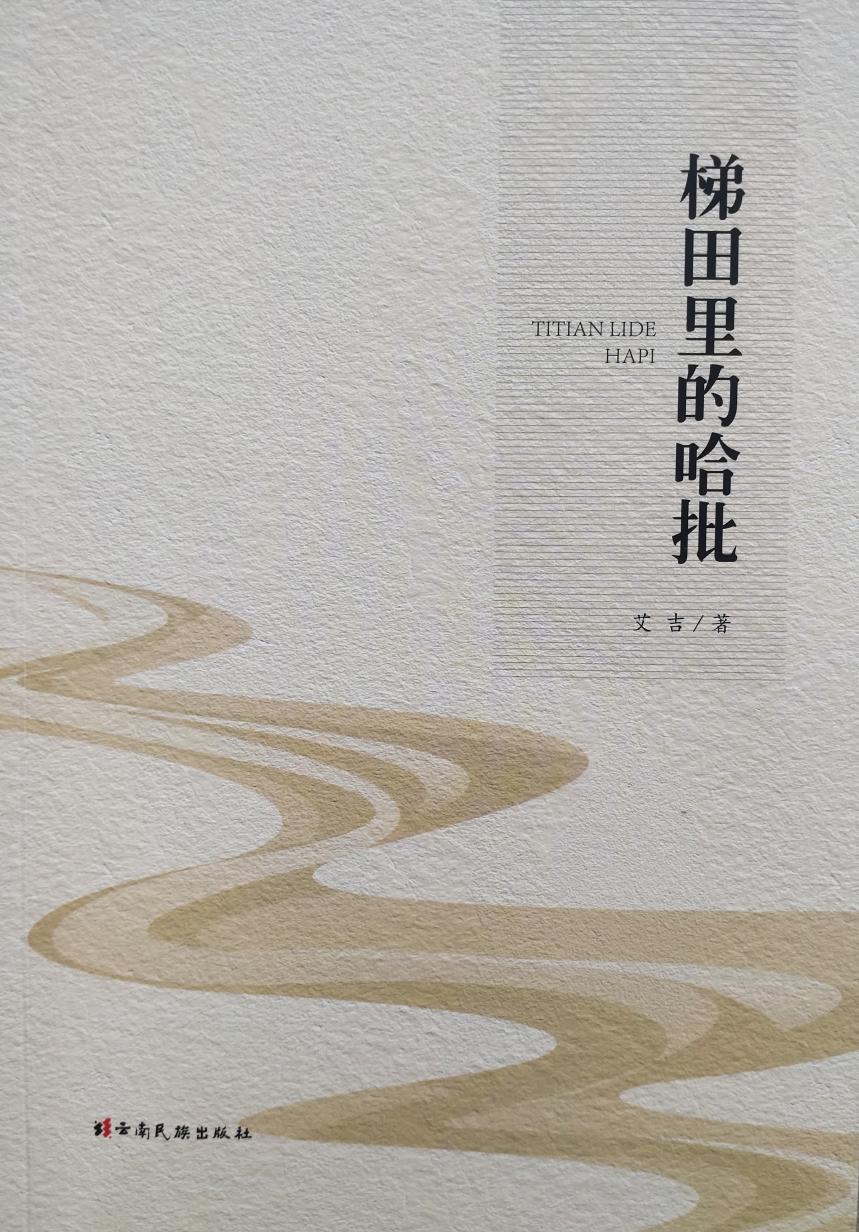
传说哈批的建立者名叫“女俄”,但没人说得出这个先祖的来龙去脉。哈批村的历史,和大多数寻常村落一样,浑似一团无法看清的迷雾。
哈批村“从热区河谷顺着一道道陡峭的山脊,一层层往上爬高的梯田,是民众以民族向自然求生存的智慧”,是无数先民历经千百年的劳作留下的文化景观遗产,“它们是破衣烂裳的无名艺术家们,神示般雕刻出的光辉之作”。
神奇的大自然,恩赐给哈批安宁而美好的人居环境:“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天空是蓝的,雾是白的,空气是干净的,庄稼是饱满的,畜禽是肥壮的,人们是相爱的”;“树林、草丛,到处住满了鸟”;哈批村的人没有征服大自然的雄心壮志,只会把大自然看作亲爹亲娘,“村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是自然的,简单的,古朴的,绿色的”。
艾吉动情地说,是梯田养育了哈批,哈批是“永世家园”。他在诗中自豪地歌唱,“我出生的村庄/浓雾拥抱梯田”;“我认识的世界/是茂密的森林/绿叶吹奏乡情,是肥沃的土地/石头也会冒油,我认识的人们/永远围着山脉/早晨走向山脚/晚上爬回山顶/弯腰劳动是最本份的姿态/诚实的心连着大地的脉搏”;“我出生的村庄/一幅青山绿水的风景/人们和神灵/一同住在安宁的居所”。
我们说《梯田上的哈批》是一部简明的农耕文明史,并非信口开河的夸大其词。对于乡土文明这个宏大的主题,艾吉选择的切口很小,他只写自己熟悉且魂牵梦萦的小山村。除了《引子》《尾声》赞美哈批之美和解说创作旨趣外,他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以《魂系梯田》《泥土人生》《亲亲自然》《回归祖先》《三大节日》《山门打开》六卷,从细微之处,将哈批的自然资源、农业生产、人文生态、民俗风情和现代生活景观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姑且不论哈尼族和梯田这两个特定的元素,艾吉所写的诸多农耕文化活动和农村传统生活习俗,显然是云南乃至整个乡土中国社会曾经拥有、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地方依然存在的乡村人文图景。
《魂系梯田》——通过对官员鱼塘、官府大田和略祖等几片具有代表性梯田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由来、耕作情况及发生在其间故事的梳理解读,譬如讲述自然梯田博物馆,庶几说清了(哈批)梯田的整体风貌及其人文价值。统而言之,在一生围着梯田转的哈批人心眼里,每片梯田都是风水宝地,这些风光旖旎的“鱼米之田”仿佛都有灵魂,他们对梯田满怀深情,“村里没有田,就没有魂了,不像寨子”——因此,一直以来,总有人“恋田恋到睡觉抱着田”,宁愿隐居在田棚,终生守望梯田;有人死后则被安葬在梯田边,魂归梯田。面对阳光照耀下雄伟壮丽的梯田,灵魂深受震撼的艾吉坚信:“祖祖辈辈的哈尼人用生命和智慧创造的梯田,永远是民族不朽的脊梁!”
在此卷中,艾吉还专门写了《梯田工具词典》和《梯田野味》,前者介绍了锄头、犁、镰刀和米箩等农具的基本形状和用途(有意思的是他将“烟筒”郑重地列入其中),后者讲述了水芹、苦果、黄鳝香柳和田蛙等二十余道梯田独有的生态野味的生长习性与制作方法。
此外,哈尼人繁多的祈福习俗、温暖的火塘文化以及集体时代的生活乐趣,都被艾吉如话家常般绘声绘色娓娓道来,读之津津有味,并不觉得啰嗦。李娟将哈萨克牧民漫长荒凉冷寂的冬牧生活写成一部温馨感人的史诗,艾吉则把哈尼人年复一年艰辛枯燥乏味的农耕生活写成甜蜜的神话。尤为匪夷所思者,是他通过追忆生产队年代集体劳动的故事,以欢快活泼的场景,将挖田栽秧之类的劳动,硬是写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狂欢娱乐”。
《泥土人生》以宽容和欢悦的口吻,一方面,讲述了农村孩子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度困匮的纯真年代,热衷玩“讨老婆”、打水仗、“猜菜”等各种游戏,以及顽童们擅长的各种偷鸡摸狗的恶作剧;另一方面,则从情感、器乐传情和乡村“奇人传”诸层面,讲述了在那个一件白衣裳就能撩动芳心的纯情时代,哈尼人日常的精神生活及人生命运。
哈呢女人勤劳善良,她们一辈了认“天命”,毕生背负一个家庭的生活。哈尼男子嗜酒,好吸烟筒,承担着开门立户的一切重活。“爱情像天空的云朵”,演绎了者木和山抽这对有情人终难成眷属的爱情悲剧:善弹三弦的者木,因家贫人穷,只能含悲忍泪弹着琴,一路眼睁睁看着“漂亮得能让村里的黑夜发光”的山抽嫁给外村人。
令人称叹的是,哈尼人天赋音乐异禀,即使未读书不识字者,大都擅以三弦、二胡、四弦、笛子等乐器传情。比如弹三弦的天才许勒斗、许拉者叔侄,前者能反弹三弦,后者可以将整个村子弹得筋骨软;罗批欧是吹笛高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才,技艺远超文工团演员;农者三的二胡、李普保的四弦、罗我收的稻笛以及白苦收的口弦,在村里都堪称一绝。在本卷中,艾吉还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为老实巴交的“阿巴尼”、“大喇叭”高峰、笑话高手唐宗耀、第一个高中生许斗保、酒鬼批处和歌手唐斗克等在村里有故事、有影响的诸人立传,塑造了若干寻常却惹人怜爱的农民形象。
《亲亲自然》盛赞哈批村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林丰泉旺鸟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哈批村的好山好水,滋养了“一群好男女,有芭蕉心白的心,有水豆腐柔的情,更有石头坚硬的脊梁”。《回归祖先》肯定了哈尼人知天乐命的生死观以及对待生老病死的豁达态度,他们按天意生活,认为死亡“不管以哪种方式走掉”,都是脱离世间苦难,相信长眠大地的人“有福了”。
《三大节日》详细介绍了人神共乐的苦扎扎、十月新年和祭寨神的风俗礼仪,这些节日充分反映了哈尼人的现实生活理想与基本信仰追求。《山门打开》反映了哈批村民从赶街子、进县城、上北京到拥向外面世界的历程,展现了哈尼人在改革开放和扶贫攻坚进程中与时俱进的新风貌。

“我的脐带/埋葬在这块土地/我的灵魂/居住在这块土地/我漂泊到哪里/带走的只是我的影子/无论我高兴或痛苦的泪水/都是献给这块土地的爱情”。信矣哉,艾吉诚然说出了一切农村赤子的心声;他确信,人有故乡且能够热爱故乡,都是幸福的。他认同吉尔吉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所说,不论你飘落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故乡——这个伟大的字眼永远是唯一的,走千里行万里,它都会使你风尘仆仆地回归,释放胸中的怀念之情。只要不断绝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那么你会一路顺风、鹏程万里。
故乡一直是艾吉写作的核心母题和重要主题。“为故乡写本不含杂质的书,告慰死去的先辈,温暖尘世的生者”,是他多年来的“狂想”。
为此,这位漂泊都市的诗人,一度时期曾反复重返故乡,不断亲近父老乡亲,走进青山碧野。
艾吉说,“我写作,实在不过是想把一些感动着我的人事、风景,用文字记录下来”;他写《梯田里的哈批》,意在为生养他的村庄“守护村魂”。而当他强烈地意识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下,与所有农村情况相似,哈尼一代年轻人外出打工,他不无忧虑地感叹,“我不是预言家,说不出梯田将来的命运”——据此而言,他倾注心血、纯粹而纯洁的书写,无疑也是为正处于新时代剧烈嬗变中的乡村招魂、铸魂。
责任编辑:目则珠江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53120240002 网络视听许可证2510473号 滇ICP备11001687号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电话、涉未成年人专用举报电话:0873-3055023 涉未成年人专用举报邮箱:hhwjjbb@163.com
中共红河州委宣传部主管 红河网版权所有 未经红河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